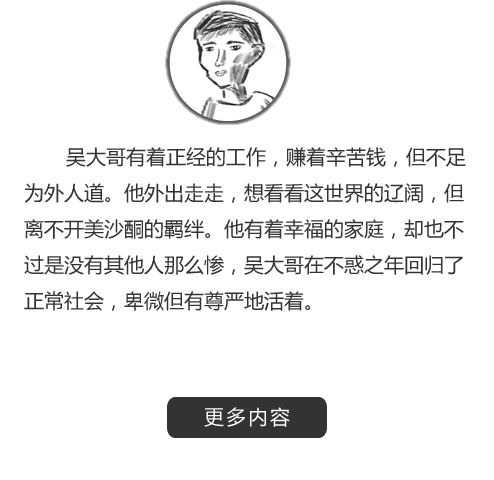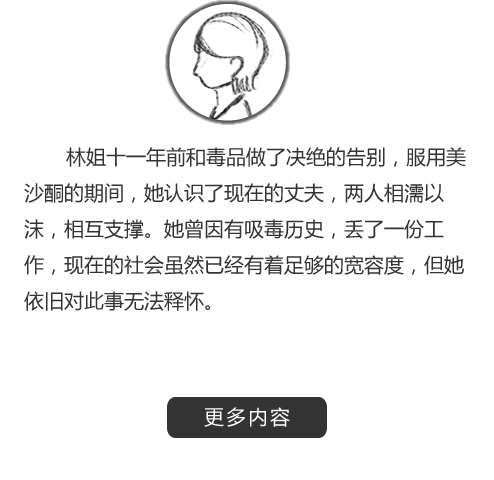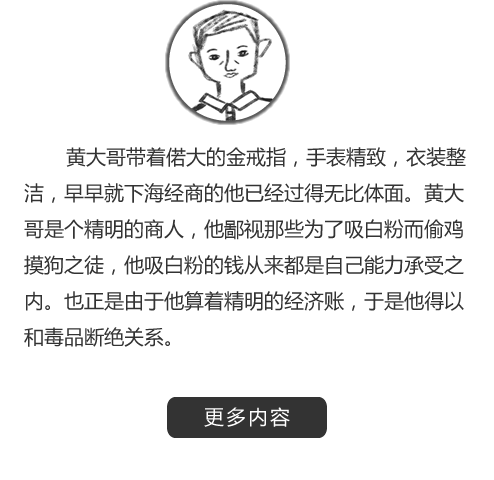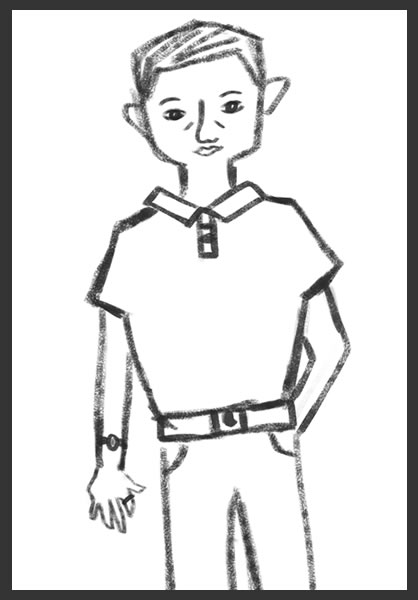王哥和桃姐是臨近門(mén)診關(guān)門(mén)的時(shí)候來(lái)喝藥的。
王哥瘦骨嶙峋,仿佛風(fēng)吹就能倒,臉色通紅,配合著黝黑的膚色,看起來(lái)像略微病態(tài)的紫色。桃姐穿著吊帶衫和熱褲,皮膚嫩白,使身上的少許紅斑越發(fā)顯眼。她臉型略浮腫,牙齒不整,但依舊彰顯著年輕的姿態(tài)。
他們是一對(duì)夫妻,王哥42歲,桃姐35歲。他們來(lái)到會(huì)客間,兩位都是煙民,便自顧自地抽上了一根香煙,王哥先說(shuō)了他的抱怨。
1994年王哥正是意氣風(fēng)發(fā)的時(shí)候,那時(shí)候的他也是在廣東闖蕩的一員,早早就開(kāi)始了發(fā)家致富,也早早就接觸了毒品。跟許多人一樣,他在無(wú)知中上了癮。桃姐是外地人,1998年在家鄉(xiāng)因?yàn)闊o(wú)知和好奇,接過(guò)了朋友手中的毒品。
“這一兩年,我時(shí)不時(shí)就被警察敲門(mén)盤(pán)問(wèn),要帶回去協(xié)助調(diào)查是否吸毒。”王哥帶著憤怒和不平說(shuō)著這句話。王哥坦言自己曾有吸毒史,在2005年開(kāi)始服用美沙酮,但沒(méi)堅(jiān)持多久就復(fù)吸白粉了,直到2010年左右才正常堅(jiān)持服用美沙酮至今。
盡管如此,他依舊飽受歧視,不時(shí)被各種騷擾,正常的工作也沒(méi)有。王哥懺悔并說(shuō)自己已經(jīng)改過(guò)自新了,為何社會(huì)還揪著他的歷史不放,處處為難他?
“上世紀(jì)90年代,一般都是大哥或者二哥才有機(jī)會(huì)吸白粉,那是身份的象征。”那個(gè)年代王哥“混得挺好”,他是個(gè)斗狠斗惡之人,1994年從少管所出來(lái)之后,他混成了“大哥”,就吸上了白粉。
他賺的錢(qián)沒(méi)有用在夜總會(huì)或者卡拉OK中,也沒(méi)有亂搞男女關(guān)系,都用在了買(mǎi)粉吸粉上。久而久之,毒品吞噬了他的身心,他走上了販毒的道路。
期間坐了多少次牢,他已經(jīng)記不清楚了,只記得要么是傷人,要么是盜竊,要么是販毒。那時(shí)候販毒的利潤(rùn)高,犯罪成本也沒(méi)這么大,況且那時(shí)候他的意識(shí)里根本沒(méi)覺(jué)得毒品會(huì)讓他傾家蕩產(chǎn)。
“我吸毒吸了幾百萬(wàn)!那時(shí)候我身邊的人都是這樣吸的,沒(méi)有人告訴我吸白粉會(huì)讓我如此窮困潦倒。”王哥怎么也沒(méi)想到,現(xiàn)在的他繼承了母親的推車(chē)小攤,賣(mài)點(diǎn)雜貨,當(dāng)年的那些老板、大哥、馬仔沒(méi)有一個(gè)人還在他身邊了。
“我去戒毒了四五次,但還是沒(méi)忍住一直在偷吸白粉。”桃姐進(jìn)了四五次戒毒所了,直到今年才正常堅(jiān)持服用美沙酮。桃姐這么多年居無(wú)定所,在各地的按摩浴足店工作,直到2009年認(rèn)識(shí)了王哥,才基本在梧州安定下來(lái)。如今的她計(jì)劃著做微商來(lái)為這個(gè)家庭增加收入。
王哥曾離過(guò)婚,帶著兒子生活已經(jīng)有14年了。
“兒子百日未過(guò),我就進(jìn)了監(jiān)獄兩年,兩年后,我出來(lái)了,兒子都兩歲多了,我和他度過(guò)了半年的時(shí)光,又因?yàn)榉甘拢M(jìn)監(jiān)獄坐了三年多,再次出來(lái),兒子已經(jīng)五歲多了。”說(shuō)起關(guān)于兒子的點(diǎn)滴,王大哥數(shù)次哽咽,臉上是無(wú)盡的悔恨和力不從心的無(wú)奈。王哥是個(gè)重情義的人,兒子是他的羈絆,也是他心里最愧疚的人,他暗暗發(fā)誓,自己無(wú)論怎樣也不能讓兒子沒(méi)飯吃。
“你們買(mǎi)白粉用一百塊就舍得,我買(mǎi)個(gè)溜溜球才六塊錢(qián),你們就買(mǎi)不起?”王哥的兒子五六歲的時(shí)候?qū)χ醺绾吞医阏f(shuō)出了這句話。王哥和桃姐都羞愧難當(dāng),心里五味雜陳,一時(shí)間說(shuō)不出話來(lái)。他們沒(méi)有和兒子過(guò)過(guò)一天幸福的日子,兒子成長(zhǎng)的時(shí)間里,王哥要么在監(jiān)獄,要么就在找毒品的路上。
“不要吸毒了!不要吸毒了!”王哥和桃姐曾經(jīng)因毒癮發(fā)作,就在家,在兒子面前吸毒。兒子走過(guò)來(lái)想拿開(kāi)針筒,撕心裂肺哭著勸他們,但沒(méi)有一個(gè)人聽(tīng)得進(jìn)一個(gè)孩子的懇求,他們像急紅了眼的怪物,用拿著針筒的那只手推開(kāi)了兒子的勸阻。
他們的人生就這樣完了?沒(méi)救了?不不不,報(bào)應(yīng)也來(lái)了,讓他們先受了報(bào)應(yīng)再離開(kāi)。
“2005年,我被檢驗(yàn)出了‘老艾’,但那時(shí)候我還不知道,直到2010年,我才正式得知自己得了‘老艾’,我的身體受不了艾滋病藥物的副作用,于是直到現(xiàn)在我也沒(méi)吃治療‘老艾’的藥物。”王哥說(shuō)出這番話的時(shí)候,已經(jīng)是絕望的神情了,面如死色。
吸毒之后,他的身體一直很虛弱,他怕,怕再吃抗艾滋的藥物,只會(huì)加速自己生命的衰竭。王哥現(xiàn)在身體的各項(xiàng)指數(shù)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不到,連擺攤都堅(jiān)持不了兩三個(gè)小時(shí)就要休息。他現(xiàn)在在倒數(shù)著死神召喚自己的時(shí)間。
“我愛(ài)他是因?yàn)楦星椋也粫?huì)因?yàn)?lsquo;老艾’而離開(kāi)他。”桃姐自然是知道王哥的情況,但桃姐沒(méi)有染上“老艾”,桃姐和王大哥小心翼翼地在一起,感情成熟之時(shí)正式于2013年結(jié)婚,并共同撫養(yǎng)王哥的兒子。
“我死后,一套20平米的房子,我的小攤,我什么都給她,雖然我也沒(méi)有什么家財(cái)了。”王哥早早就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,桃姐也欣然接受了他的安排,對(duì)于命運(yùn)、報(bào)應(yīng),他們都在承受著他們應(yīng)該承受的。
“別碰毒品,一碰就沒(méi)救了,沒(méi)救了,沒(méi)救了。”這是他們離開(kāi)時(shí)最后對(duì)記者說(shuō)的話。